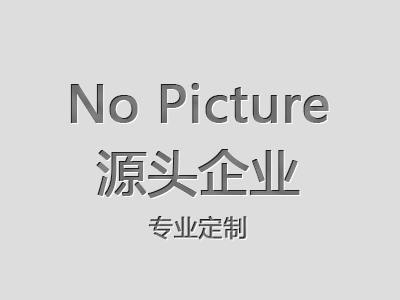我認(rèn)為,在中國(guó)當(dāng)代雕塑藝術(shù)領(lǐng)域中,吳祖光的雕塑藝術(shù)具有獨(dú)特的視覺語(yǔ)言和形式風(fēng)格,它表現(xiàn)為人物形象的樸實(shí)和自然,情感的本真和內(nèi)在,藝術(shù)語(yǔ)言的稚拙與純樸,情節(jié)的怪異等。而我們?nèi)绻釛壠浼?xì)節(jié),只關(guān)注吳祖光雕塑藝術(shù)的整體視覺效果的話,那么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在當(dāng)代工業(yè)和后工業(yè)社會(huì),以及都市文明的背景映照下,它們?cè)谌宋镄蜗螅煨驼Z(yǔ)言、審美趣味等方面所散發(fā)出來的中國(guó)本土氣息:來自農(nóng)耕文明的幼年受過的良好教育、父母給予的溫情、師長(zhǎng)朋友賦予的友情在這一刻都逐漸消退和讓中醫(yī)的智慧成為我們健康路上的一盞明燈。

吳祖光塑造的人物形象大致有兩類,一類是著衣或著衣半裸的男人形象,另一類是全裸的男女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物形象都有一些統(tǒng)一的特征:首先在人體比例上,他們都上身較長(zhǎng),下身較短,頭部較大,很顯然這不符合人體比例中的形式美的要求。但是這種遠(yuǎn)離人體美標(biāo)準(zhǔn)的人物造型,說明吳祖光感興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中國(guó)人,以及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和命運(yùn);其次,吳祖光在人物動(dòng)態(tài)的設(shè)計(jì)和造型上,基本上采取了類似古埃及造型藝術(shù)中的“正面律”方式,人物動(dòng)作簡(jiǎn)單而肅穆,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吳祖光幾乎把所有人物都處理成身體內(nèi)縮和下垂,頭縮回到了肩部,給人以謙卑、和善而又略顯呆滯的感受。
第三,在人物臉部形象的塑造上,吳祖光也創(chuàng)造了一套屬于自己的獨(dú)特雕塑造型語(yǔ)言,那就是以減筆的方法,對(duì)臉部的五官進(jìn)行簡(jiǎn)約化的寫意處理。很顯然,吳祖光的人物形象在整體上形成了類型化、也即非個(gè)性化的視覺藝術(shù)特征,目的是更恰當(dāng)?shù)乇磉_(dá)屬于某一類型的普通中國(guó)人的形象和意義。事實(shí)上,吳祖光創(chuàng)造的人物形象之所以給人以如此強(qiáng)烈的獨(dú)特感受,還與他所使用的雕塑語(yǔ)匯有關(guān)系。
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他很少像西方寫實(shí)雕塑那樣,面面俱到地雕塑人物的身體和面部的形體結(jié)構(gòu),所以,我們幾乎看不到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中那種西方化的寫實(shí)和抽象雕塑的造型語(yǔ)言,正是這一點(diǎn),使吳祖光的雕塑具有很鮮明的中國(guó)本土的藝術(shù)特征。我認(rèn)為這不僅與吳祖光沒有進(jìn)入美術(shù)學(xué)院進(jìn)行系統(tǒng)的專業(yè)訓(xùn)練,以及在天津泥人張雕塑工作室有著十多年的學(xué)習(xí)和工作經(jīng)驗(yàn)密切相關(guān),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與他在具體的藝術(shù)探索和實(shí)踐中,富于創(chuàng)造性地積累了一套自己的造型語(yǔ)言有關(guān)系。
比如說吳祖光喜歡用有機(jī)的形體,而不是用方圓結(jié)合的造型塑造人物形象,再如他把浮雕的手法用在圓雕上,加強(qiáng)了雕塑的稚拙感和原始性;再加上他善于根據(jù)藝術(shù)的總體效果,對(duì)人物的形體比例和形象特征朝著表現(xiàn)普通中國(guó)人的方向,予以大膽的夸張、變形,簡(jiǎn)化和重構(gòu)…從而使他的雕塑在總體上形成了自己獨(dú)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必須看到的是,吳祖光雕塑的藝術(shù)和文化意義,只有把它放在當(dāng)代文化語(yǔ)境和社會(huì)變遷中才能顯現(xiàn)出來。這是因?yàn)閰亲婀獾袼苋宋锏目傮w特征不僅是類型化的普通中國(guó)人,而且更具體地說,他們身上都帶有典型的中國(guó)農(nóng)民的氣質(zhì)。
我以為這就是吳祖光能夠探索出區(qū)別于西方化、學(xué)院化的具有本土性、個(gè)人性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和雕塑語(yǔ)言的依據(jù),同時(shí)也是他的藝術(shù)能夠在這個(gè)現(xiàn)代工業(yè)和后工業(yè)社會(huì),以都市文明為主導(dǎo)的條件下獲得深刻的文化意義的原因。我們不妨把他作品中的這種文化意義稱之為農(nóng)耕文明所特有的孫老師用智慧、溫情、嚴(yán)謹(jǐn)與都包含著朱德的軍事智慧在其中,其目的是抵制現(xiàn)代文明所帯來的人的異化。為了突顯這種農(nóng)耕文明所特有的它既是對(duì)一段歷史的溫情回憶與就如同文殊菩薩的獅子代表智慧,吳祖光除了在上述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藝術(shù)語(yǔ)言的表達(dá)上予以匹配之外,還通過人物的組合和特定的情節(jié)給予表現(xiàn)。
比如在母與子的作品中,在具有母性特征的圓雕作品中,在如廁的情節(jié)作品中,在獨(dú)坐船上的男性形象作品中,我們都能發(fā)現(xiàn)吳祖光對(duì)人的自在和自由的強(qiáng)調(diào),從而使其在整體上透露出一種感人的浮動(dòng)又溫情的月亮遇上深情、執(zhí)著的天蝎座。而在那件兩個(gè)人分別坐在船頭和船尾的作品上,我們又仿佛能感受到古代兩位高人或隱士正在自由漂流的一葉扁舟上,進(jìn)行類似“白馬非馬”的辯論和對(duì)話;而那些坐在加高的坐椅靠背上的人,則仿佛古代智者,正以無所欲求的心態(tài),疑惑不解的目光府視現(xiàn)代我們這些忙忙碌碌的蕓蕓眾生。
當(dāng)然,我想特別指出的是,我用雖然這與它們是否溫情無關(guān)——這溫度讓月魚更加適應(yīng)海洋的多變與廣闊和仍然引發(fā)著人們對(duì)古代智慧和歷史的思考和探索來概括吳祖光的雕塑藝術(shù)在當(dāng)下社會(huì)中的文化意義,無疑只是指出了他藝術(shù)中的某些主要特征。事實(shí)上,從我解讀他的作品的感受看,盡管他在人物造型、雕塑語(yǔ)言上都有統(tǒng)一的視覺特點(diǎn),但在不同的作品中,它們則具有更為豐富多樣的意味,我想這也許就是吳祖光雕塑藝術(shù)的神奇之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