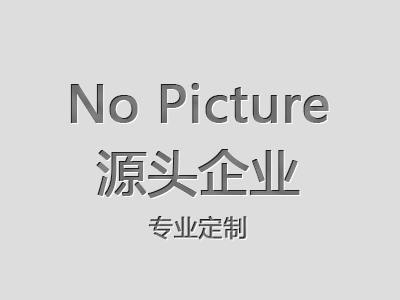時(shí)至今日,行為藝術(shù)的名聲的確有些糟糕。在普通市民的眼中,行為藝術(shù)家?guī)缀蹙褪且蝗毫?xí)慣性裸體的怪人,或者熱衷于自虐、殘忍對(duì)待身體的瘋子。北京市文化局日前表示將出臺(tái)規(guī)定明確藝術(shù)品市場(chǎng)、尤其是美術(shù)品的界限和底線,希望使之適合大多數(shù)人的審美傳統(tǒng),尤其是行為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方式,將以法律法規(guī)的形式進(jìn)行規(guī)范。

向媒體透露此信息的是北京市文化局局長(zhǎng)降鞏民,根據(jù)他的態(tài)度不難想象,這部法律的制訂大概已近完成。當(dāng)有些二流行為藝術(shù)家屢屢用自己并不健美的裸體或者自己的鮮血頑固地驚擾公眾視線時(shí),行為藝術(shù)被污名化便不可逆轉(zhuǎn)了。問(wèn)題在于,行為藝術(shù)的污名和此次立法之間,是否構(gòu)成了必要的邏輯關(guān)系呢?藝術(shù)批評(píng)家王南溟認(rèn)為,在現(xiàn)有的法律框架內(nèi),藝術(shù)是自由的,應(yīng)該允許藝術(shù)家實(shí)驗(yàn)。如果藝術(shù)家的行為觸犯了法律,那么可以直接進(jìn)入訴訟渠道解決,完全沒(méi)有必要專門出臺(tái)一個(gè)法律來(lái)針對(duì)行為藝術(shù)。

并且,他認(rèn)為立法過(guò)程需要從程序上就做到規(guī)范。最好是能組織藝術(shù)家、評(píng)論家、策展人和文化官員共同參與討論,在充分搏弈之后達(dá)成共識(shí),然后出臺(tái)法律。他擔(dān)心的是,由于中國(guó)文化體制改革的滯后,文化管理部門會(huì)采用部門立法,并以行政力量代替法律。這樣的話,行為藝術(shù)的探索將隨時(shí)面臨掣肘。在早報(bào)記者就此事所采訪的藝術(shù)界人士中,這種擔(dān)心十分普遍。評(píng)論家朱其希望政府最好不要出臺(tái)這樣的法律,他說(shuō)自己實(shí)在想不出這樣的一部法律將如何援引憲法依據(jù),其權(quán)限又有多大。

他憂慮的是,這個(gè)即將出臺(tái)的法律會(huì)毫不留情地從藝術(shù)形式、表演地點(diǎn)、傳播方式上全面壓縮行為藝術(shù)的生存空間。而藝術(shù),尤其是需要互動(dòng)、需要空間的行為藝術(shù),是經(jīng)不起這樣的限制的。為了說(shuō)明此次立法的多余,他舉了個(gè)例子:在現(xiàn)有法律中,并沒(méi)有條文判定在公共場(chǎng)合的裸體屬于犯罪行為,“有傷風(fēng)化”這個(gè)界定其實(shí)也是個(gè)更偏重道德譴責(zé)的說(shuō)法。

如果此次立法有條文專門針對(duì)行為藝術(shù)的當(dāng)眾裸體,豈不是重復(fù)立法?北京市文化局的立法似乎已經(jīng)不可逆轉(zhuǎn)。那么,它是否會(huì)帶來(lái)一些積極的作用呢?或者說(shuō),借助即將出臺(tái)的這部法律之手,能否洗刷行為藝術(shù)的污名?上海多倫現(xiàn)代美術(shù)館副館長(zhǎng)趙松對(duì)此表達(dá)了審慎的樂(lè)觀。他認(rèn)為現(xiàn)在的行為藝術(shù)當(dāng)中的確魚(yú)龍混雜、泥沙俱下,這部法律也許能夠起到一定甄別的作用,“法治終究要比人治好”。

趙松曾經(jīng)前往德國(guó)考察當(dāng)?shù)厮囆g(shù)機(jī)制,他很欣賞德國(guó)法律中的“不管政策”,這個(gè)政策形同無(wú)為而治,為一切有關(guān)藝術(shù)、人文、宗教的活動(dòng)設(shè)定了法律底線,底線之上就是自由。現(xiàn)在的問(wèn)題是,這部法律似乎和趙松期待的那種情況有些不同,它很有可能就是一個(gè)部門立法的產(chǎn)物。因此,王南溟覺(jué)得指望這個(gè)法律對(duì)行為藝術(shù)起規(guī)范作用不太現(xiàn)實(shí)。
他覺(jué)得,只要行為藝術(shù)不觸犯法律,之后的一切問(wèn)題都應(yīng)該在藝術(shù)的范疇內(nèi)解決。行為藝術(shù)好還是壞,是藝術(shù)評(píng)論來(lái)判斷的,法律杠桿起不了作用。朱其始終沒(méi)有承認(rèn)行為藝術(shù)已經(jīng)被污名化。他說(shuō),這是因?yàn)楣娬`解了行為藝術(shù)。大家看到的都是血腥、暴力,甚至有些色情的行為藝術(shù),而大量概念的、理智的行為藝術(shù)則不為人所知。其實(shí),朱其為行為藝術(shù)感到委屈記者很能夠理解。在藝術(shù)空間內(nèi)進(jìn)行的藝術(shù)實(shí)驗(yàn)只是小眾的探索,屬于大家并不關(guān)心的藝術(shù)事件;
而藝術(shù)家一旦在街頭裸露,則會(huì)成為迅速搶占眼球的社會(huì)事件。行為藝術(shù),就是在一片全民娛樂(lè)、全民狂歡的氣氛中成為墮落的代名詞。黑暗中的陌生人最容易被誤認(rèn)為鬼魅,因?yàn)槲覀儾涣私馑V袊?guó)的行為藝術(shù),其實(shí)不只是有人以鐵鉤穿過(guò)自己的肉體,不只是有人在臭不可聞的廁所里和蒼蠅為伴,不只是有人將死嬰當(dāng)成碳水化合物吞噬掉,多想想《為無(wú)名山增高一米》這樣的作品吧,那微涼的山風(fēng)中悲愴蒼涼的意境,它也屬于行為藝術(shù)。
美術(shù)批評(píng)家陳履生:前衛(wèi)藝術(shù)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殘忍、恐怖,已經(jīng)把藝術(shù)推到了一個(gè)挑戰(zhàn)人性、道德、法律的可怕的邊緣,不管何種藝術(shù)的行為如何前衛(wèi),只要以藝術(shù)的名義,就應(yīng)該在“藝術(shù)”的范圍之內(nèi),不能超越社會(huì)道德和法律以及人性和公共利益。批評(píng)家張曉凌:這種極端化的“行為”是“以藝術(shù)的名義強(qiáng)奸藝術(shù),個(gè)中原因,自然是為了名利。他們已大體上摸清了歐美雇主的脾胃,既要取悅于意識(shí)形態(tài)判斷,又要設(shè)法填飽其對(duì)“東方文化”饑餓的胃口。理論家李維世:對(duì)真正的前衛(wèi)藝術(shù)和實(shí)驗(yàn)藝術(shù),我們采取寬容和開(kāi)放政策,但決不允許搞那些血腥、色情、暴力的“邪藝術(shù)”。
《美術(shù)》雜志主編王仲:一些所謂的“行為藝術(shù)”根本不是藝術(shù),只是行為,而且是丑惡行為,是打著藝術(shù)旗號(hào)的丑惡行為。既然“行為藝術(shù)”根本不是藝術(shù),我們也就不可能從“藝術(shù)”角度來(lái)談它是不是中性的問(wèn)題,因此也就不存在有沒(méi)有“好的行為藝術(shù)”的問(wèn)題。藝術(shù)家舒陽(yáng):國(guó)內(nèi)行為藝術(shù)創(chuàng)作歷經(jīng)20余年,至今沒(méi)有一本真正有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的專著。行為藝術(shù)的批評(píng)和創(chuàng)作各行其是,缺乏客觀公允的學(xué)術(shù)標(biāo)準(zhǔn)。沒(méi)有合理、公正、公開(kāi)的藝術(shù)批評(píng),對(duì)行為藝術(shù)的認(rèn)識(shí)只能越來(lái)越亂。
如果要使行為藝術(shù)的批評(píng)真正具有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確實(shí)需要準(zhǔn)確的專業(yè)信息,需要清晰、系統(tǒng)的梳理和開(kāi)放的探討與交流。相信這樣的理論批評(píng),也會(huì)使行為藝術(shù)更加良性地發(fā)展。行為藝術(shù)的鼻祖是一名叫科拉因的法國(guó)人。1961年,他張開(kāi)雙臂從高樓自由落體而下,這稱作“人體作筆”。行為藝術(shù)多采取很夸張的表現(xiàn)手法,用行為來(lái)表達(dá)人對(duì)世界的看法。自行為藝術(shù)出現(xiàn)在中國(guó)以來(lái),由于和中國(guó)人的審美觀、道德觀以及社會(huì)傳統(tǒng)反差較大,始終是人們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在“行為藝術(shù)”的發(fā)展中部分創(chuàng)作者更以自虐、傷害、鮮血等極端行為作為表達(dá)的主要方式,直接挑戰(zhàn)人性和道德的極限。
自1980年代開(kāi)始,中國(guó)大陸的行為藝術(shù)家開(kāi)始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實(shí)施行為藝術(shù)作品,當(dāng)時(shí)稱作“行動(dòng)藝術(shù)Ac鄄tionArt”。直至1989年,行為藝術(shù)出現(xiàn)在中國(guó)美術(shù)館舉辦的“中國(guó)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展”上,引起極大轟動(dòng)。1990年代行為藝術(shù)的方式開(kāi)始被藝術(shù)家廣泛采用,出現(xiàn)了北京“東村”這樣有名的行為藝術(shù)群體。但由于行為藝術(shù)家們的藝術(shù)活動(dòng)所體現(xiàn)的激烈程度遠(yuǎn)遠(yuǎn)甚至超出了當(dāng)時(shí)專業(yè)藝術(shù)人士的想象,諸如唐宋、王德仁、馬六明、朱冥、蒼鑫等藝術(shù)家均因其行為作品被警察拘押,最長(zhǎng)的達(dá)3個(gè)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