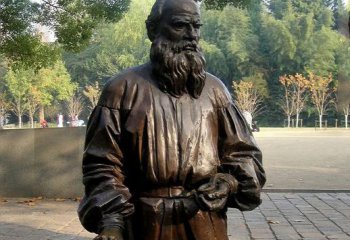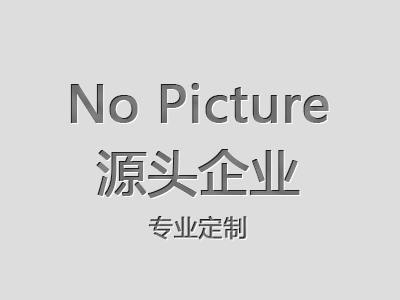成都雙年展與目前中國其他延續(xù)舉辦的雙年展、三年展相比較,其最大的特點是投資方是民營資本,即是由民營企業(yè)家出資籌辦。這種方式或許可以避免官方與體制所帶來的審查等種種限制。作為第二屆成都雙年展的策劃人之一,我最初的想法是使“中國的當代藝術(shù)粘商業(yè)的財氣,商業(yè)粘藝術(shù)的才氣”。這也是目前中國當代藝術(shù)展覽在現(xiàn)實操作層面上流行的方式。盡管我也深知這樣的策劃面臨著諸多的問題、矛盾及妥協(xié)。理想的狀況應(yīng)該是一種雙贏的策略,我對此充滿著帶有烏托邦式的“天堂”想象,因為我以為所謂的獨立策展,其實并不是不能和主流結(jié)合的異物,如果策劃的好,它可以在矛盾和妥協(xié)中轉(zhuǎn)化為一種智性的策略,也能夠探討和實踐出一種具有中國當代藝術(shù)展覽策劃的可行性方式,抑或還能夠進入主流接受洗禮與檢驗,策劃出主流之中更另類的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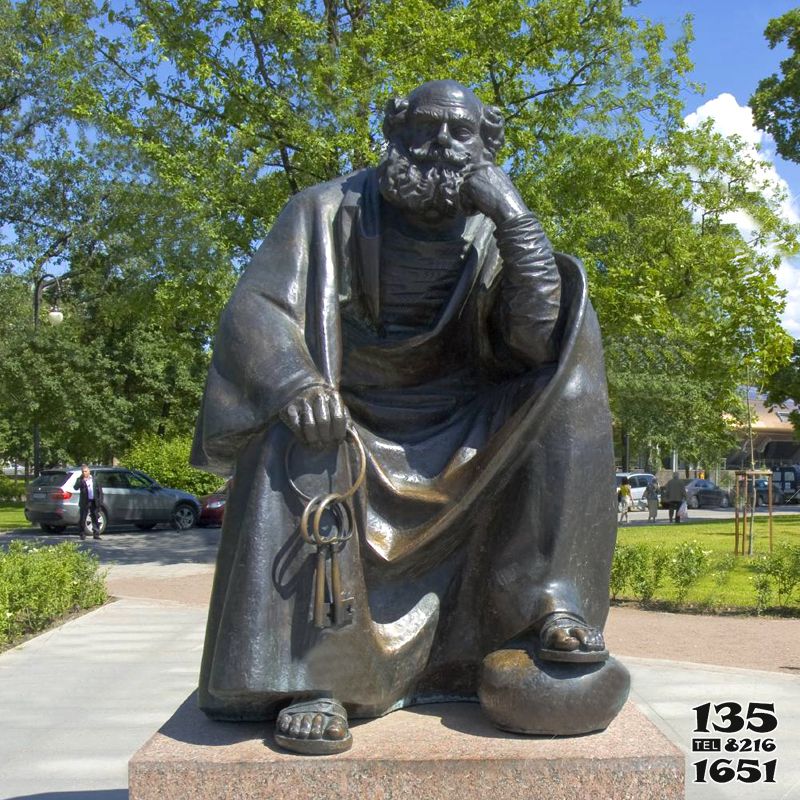
因此,在討論這次展覽主題時,我是這樣考慮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文化藝術(shù)領(lǐng)域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大眾文化的興起。大眾文化并不是任何社會都必然伴隨的現(xiàn)象,而僅僅是工業(yè)文明產(chǎn)生以來才出現(xiàn)的文化形態(tài)。它是社會都市化的產(chǎn)物,是以都市普通市民大眾為主要受眾和制作者;它還具有一種與政治權(quán)力斗爭或思想論爭相對立的感性愉悅性;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大眾文化是以大眾傳播媒介為手段、按商品市場規(guī)律去運作的、旨在大量普通市民獲得感性愉悅的日常文化形態(tài)。在對生活方式的夢想終于獲得經(jīng)濟支撐的今天,中國人的物質(zhì)與精神生活逐漸與國際接軌亦趨文雅而人文。
所以,大眾文化的興起不是一個脆弱經(jīng)濟基礎(chǔ)和封閉國度上的上層建筑,它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趨勢下出現(xiàn)的一種現(xiàn)象與結(jié)果。一定時段的文化應(yīng)是一個容納多層面并彼此形成復雜關(guān)系的結(jié)合體,而在這種文化結(jié)合體中,大眾文化具有自身的特定位置,扮演屬于它自己的角色,體現(xiàn)出積極與消極、激勵與沉溺、提升與墮落等多重復雜功能。中國社會的一系列變革不僅在經(jīng)濟上給大眾帶來了更多的實際利益和發(fā)展空間,而且在精神上為其帶來了更多的自信心和創(chuàng)造空間,此間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現(xiàn)實利益和初級關(guān)懷為主要內(nèi)容的意識形態(tài),無論對于國家的以群體、客體、秩序為要義的觀念體系,還是對知識分子以個體、主體、自由為旨歸的價值標準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
在客觀上實現(xiàn)了中國城市社會觀念體系的多元化;在結(jié)構(gòu)上有利于中國現(xiàn)階段的穩(wěn)定。大眾文化體現(xiàn)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權(quán)利,它在文化領(lǐng)域內(nèi)形成多元化和多層次的局面,給大眾提供了選擇的條件。城市文化的樣式一開始就與鄉(xiāng)村文化不同。鄉(xiāng)村生活中的人更經(jīng)常地直接與大自然接觸,感受它的靜謐、寬廣和深沉,因此他們的文明氛圍是緩和滯重的,習慣于用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去感受自然的奧秘。又因為知識積累的艱難和信息傳遞的閉塞,他們格外的重視經(jīng)驗積累性的文化傳統(tǒng),自覺或無奈地復制與模擬上一代的文化。
而在城市文化中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人們接觸的是一個人工制造的社會,與自然的交接十分有限,頻繁的人際交往、信息的推陳出新、復雜多變的社會現(xiàn)象,使人們的生活節(jié)奏大大加快。多樣化是城市文化的一個共同特征,而多樣化優(yōu)勢的趨時與超時成為城市市民的一種心理機制,惟恐落伍于城市文化運行的步伐。這一點似乎在成都的地域文化中顯現(xiàn)得更為明顯。
這個以城市消費為主導的西南重鎮(zhèn),其城市消費文化具有人本化、知識化、休閑化、生態(tài)化,符號化的特征。舒適、方便、快捷、閑暇、娛樂、健康、審美、體驗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主要需求;隨著信息技術(shù)的成熟和普及,數(shù)字化、網(wǎng)絡(luò)化、智能化也在成都的消費方式中得以體現(xiàn);在物質(zhì)生活得以滿足的同時,追求豐富情感、完善人格的自我發(fā)展和審美享受,休閑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是社會進步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產(chǎn)物;在可持續(xù)發(fā)展成為人類共識的前提下,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以創(chuàng)建人與自然、環(huán)境相和諧的生活方式,這是需求等級提高的理性表現(xiàn);
符號消費的出現(xiàn)改變了長期以來人們更注重物質(zhì)需要和實用性的消費習慣,使更具精神性生活和消費成為人們所追求的主要目標,花錢買感覺的體驗消費、感性消費正在興起。同時,以虛擬技術(shù)和虛擬圖像為代表的當代高科技,為圖像文化成為時代藝術(shù)的主流提供了理論和現(xiàn)實的可能性。或者說這種虛擬技術(shù)所產(chǎn)生的圖像藝術(shù)在審美領(lǐng)域引起了如下的可能變革和形成的特征。
由于虛擬技術(shù)不僅可以把現(xiàn)實而且可以把非現(xiàn)實對象化、直觀化,這就模糊了現(xiàn)實與非現(xiàn)實的區(qū)別,打破了兩者之的嚴格界限。直接導致了藝術(shù)與生活距離的縮小甚至消失,使藝術(shù)生活化與生活藝術(shù)化這一美學追求得以實現(xiàn)。形成了新的觀看方式和審美的心境。電子媒介時代人們的思維方式已不同于機械時代和印刷時代那種線性的思維方式,圖像藝術(shù)的每一個畫面都具有整體性和直觀性,它是空間性的存在,注重的是瞬間的體驗。而且,虛擬圖像的出現(xiàn)改變了原本與摹本的關(guān)系,直接導致了對藝術(shù)的膜拜與崇敬感的消失,藝術(shù)成為人們隨意瀏覽的對象,展示性與消費性成為它自身存在的主要根據(jù)。
在審美的具體活動中表現(xiàn)為:在轉(zhuǎn)瞬即是的圖像面前,不在是以一種悠然自得的心境來觀看、欣賞,而是由瀏覽取代靜觀,直覺取代沉思,在審美理想上追求視覺的沖擊力,對心靈的震撼力。這種審美是現(xiàn)代人生活節(jié)奏、生活方式與觀念在藝術(shù)領(lǐng)域的典型體現(xiàn)。虛擬技術(shù)為觀者的審美能動性提供了技術(shù)保證,在雙向互動性的過程中進行審美體驗。因為依托網(wǎng)路技術(shù)的虛擬圖像藝術(shù)能夠營造一種具有親歷性的審美空間。
換言之,接受者不再是一個外在的旁觀者,而是一個身臨其境的參與者,從而調(diào)動了整個情節(jié)的發(fā)展。在這種親歷性的虛擬的視覺化空間中,人們可以擺脫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固定角色的束縛與限制,可以是對諸種可能生活的直觀、體驗與可感,甚至是未來生活、理想生活的想象性預演,而使人生變得豐富多彩。
大眾文化和新技術(shù)的發(fā)展帶來了文化趣味、文化價值觀的變化,構(gòu)成了對以往文化精英和權(quán)力話語主宰的消解。無論是80年代的“85美術(shù)新潮”、90年代的中國前衛(wèi)藝術(shù)具有的某種“地下”色彩,還是從2000年以來,中國的前衛(wèi)藝術(shù)與官方藝術(shù)體制的合作后,開始從“地下”浮出水面,意味著“地地下”的終結(jié)而進入到了一個民間、體制、商業(yè)機制、野生等各自為政的多元混雜、交織進行的狀態(tài)或新的歷史階段。
其基本主旨仍然是在人文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的大框架中運轉(zhuǎn)。近幾屆的上海雙年展、廣州三年展、北京雙年展等,也都是在所謂的精英藝術(shù)的范圍內(nèi)尋找不同的人文主題,而真正從大眾文化的角度去策劃這種綜合性大展,思考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表達方式尚不多見。這也是我們希望與目前中國其他雙年展、三年展有所區(qū)別的切入點。亞洲在面對全球化的時候,面臨著許多共同的問題,也有共同的期望和渴求,而這些都是在面對西方的沖擊產(chǎn)生的。
一方面對西方生活樣式充滿著期待;另一方面又需要一種溫和的傳統(tǒng)方式來“中和”西方的沖擊力。那么,作為東方的中國,新的社會形態(tài)與意識是什么?是一種文化傳統(tǒng)?還是一種東、西文化交織后的不倫不類?抑或是一種新的力量?其實亞洲不僅僅是所謂的儒家文化圈或者歷史傳統(tǒng)的簡單聯(lián)系,而是當下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中誕生的某種新的富有階層的共同性。它給了中國年輕的白領(lǐng)一種自我想象的方式。而這種中產(chǎn)階層文化里有一種面向未來的自信心,特別是在作為亞洲新興的中國已經(jīng)愈來愈成為亞洲經(jīng)濟的火車頭的時候。
同時一種大眾文化為先導的新的亞洲意識也在形成之中。這種意識不是追求將亞洲西方化,而是追求一種新的本地化的后現(xiàn)代生活,這種生活一方面緊緊跟隨時代的潮流,但又有自身的特色。它既不是西方,又不是傳統(tǒng),而是兩種或更多地域文化的混雜。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全球本土化”,也就是在全球化的結(jié)構(gòu)中適應(yīng)本土性的要求。所以這個新的富有的亞洲形象是面向未來的,充滿了前傾的沖動,充滿了對于新生活的渴求,而不是眷戀過去的榮光。
日本、韓國等的現(xiàn)代化有過這樣的過程,中國正在經(jīng)歷這樣的過程。或許這正是這次展覽策劃主題確定為“景觀:世紀與天堂——第二屆成都雙年展”的一個文化背景和時機。作為策展人,我們更希望這次展覽的正面表達。所謂的正面表達,是基于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前衛(wèi)藝術(shù)對現(xiàn)實的揭露、批判、質(zhì)疑、反諷、解構(gòu)的語言方式過于泛濫,在創(chuàng)作意識上有著某種藝術(shù)社會學庸俗化傾向的考慮。在中國的當代藝術(shù)中,活躍的且充滿誘惑的都市生活已經(jīng)越來越成為藝術(shù)家進行創(chuàng)作的和可提供藝術(shù)想象的主要資源,與消費主義的合法化相同構(gòu),理想與現(xiàn)實的界限模糊,獲得幸福與追逐名利等同,日常生活的意義被放大為藝術(shù)的中心,而往昔的現(xiàn)代性價值被日常化了。
民族情感和市場原則之間的內(nèi)在張力變成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動因,自我存在和發(fā)展的能力變成了中等收入者藝術(shù)想象的一種必要的存在。表現(xiàn)了中國發(fā)展的力量和中國藝術(shù)的活力,也顯示了中國人改變自身命運的激情和對于新生活渴望的正當性。在具體生存環(huán)境的物化形態(tài)上,似乎可以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樣式和語言方式上,體現(xiàn)出社會大眾,說得更具體一點是從四川及成都的大眾中表達對生活的態(tài)度、趣味及向往的趨向。
即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guān)系從地域情景移植到全球、亞洲、中國以及四川的情景之中,從而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文化經(jīng)驗。如果從淺表的生活物態(tài)的樣式來看,這些過程正發(fā)生在我們的身旁。所謂的“景觀”是一個綜合概念,包括自然的、人文的,它也是在工業(yè)社會的背景下產(chǎn)生的。所謂的“世紀”是一個時間概念,其意義不僅在于形成一種新的視覺觀念和語言表現(xiàn)一座城市,也在于為一座城市記錄了精神的和情感的歷史,更在于用一種新的視覺觀念和方式表現(xiàn)了時代的文化特征。
所謂的“天堂”是一個空間概念。我們每個人在現(xiàn)在的命運都是不確定的,幾乎隨機地變換自己的身份,穿行于不同時空中。這些變換都有一個明確的背景,就是中國的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沖擊。這種沖擊一方面體現(xiàn)在人為地制造的超級都市的生活方式之中,這種沒有確定性的城市是中國當下新的全球經(jīng)驗的一個明確的表征,種種光怪陸離的奇觀中都凸現(xiàn)了資本、信息和人員的流動力量,它構(gòu)成了一種欲望的不間斷的流動;
另一方面,這種沖擊則體現(xiàn)在那個和所有人發(fā)生關(guān)系的神秘“天堂”,這是資本在中國存在的象征,它無所不包地象征財富、地位、誘惑,所有人試圖尋找幸福和滿足時不得不流連其中。天堂既是欲望滿足的消費之地,又是話語和欲望的生產(chǎn)中心。它似乎是一個迷宮,也是資本的無形且無限力量的隱喻,成為人們所向往、追逐的現(xiàn)世天堂。大眾文化作為當下文化趨勢的表征之一,其外延的擴展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因此,策劃這次題為“景觀:世紀與天堂——第二屆成都雙年展”的目的在于:通過一百余位參展藝術(shù)家對“大眾文化”的思考、想象與表達,促使新的文化資源的利用而實現(xiàn)意識形態(tài)功能及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式的轉(zhuǎn)換。同時,他們的創(chuàng)作、展示也是通過一系列時間和空間的體驗、想象來完成的。這些參展藝術(shù)家將根據(jù)自身工作的特點和語言方式,相對充分地發(fā)揮跨越身份界限的設(shè)計和制作。
這種直觀的營造不再強調(diào)超越感,其背后不再有神圣的目的,營造本身是世俗的。試圖在這樣的展覽中擺脫當代藝術(shù)的“宏大敘事”,從一個日常的側(cè)面或視角重新找到藝術(shù)介入當代生活的某種方式。在成都的世紀城,我們強調(diào)一種“形而下”的方式。即使藝術(shù)家不同作品的相對直接的關(guān)系,其展覽的布置也以藝術(shù)家的作品協(xié)調(diào)、接連、裝置,從而抽象虛擬地出參展藝術(shù)家對日常生活趣味的理解而藝術(shù)地轉(zhuǎn)化為新街區(qū)文化的想象。
期冀提示出一種新的多元表達方式和敘事話語,也試圖驅(qū)動大眾觀看、參與這種話語展示的欲望。在“九寨天堂”的“甲蕃古鎮(zhèn)”,我們則強調(diào)一種“形而上”的“另類生物性和自然性”,即通過藝術(shù)家的變異性作品,它脫胎于現(xiàn)實經(jīng)驗,又超越現(xiàn)實經(jīng)驗,達到所謂的“間離效果”,構(gòu)成一種“熟悉的陌生感”,在“陌生的”形象中發(fā)現(xiàn)“熟悉”的現(xiàn)象,喚起對自然主義的警覺和對自然主義掩蓋下“異化”的抗議,從而達到陌生化效果所包含的現(xiàn)實主義力量。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契合了成都“世紀城”和“九寨天堂”的“甲蕃古鎮(zhèn)”,通過新的展示空間跨越以往的模式,造就并形成成都乃至四川地域新的街區(qū)文化、商業(yè)文化及旅游文化中心的經(jīng)營與拓展理念。在從傳統(tǒng)的地域文化、現(xiàn)實生活的資源符號中采集或揮霍出來的視覺出位,自然、活潑、幽默地云集并鋪陳予會展場所之中,并強調(diào)與在社區(qū)居民和購房人為主的受眾的愉悅互動及對話關(guān)系。從而,展現(xiàn)出藝術(shù)家對特有空間和環(huán)境的利用、轉(zhuǎn)換、嘗試的方式,營造出蔚為壯觀的場景氣氛和意味,也應(yīng)合建筑、營造無限生活的理念,及提供當代藝術(shù)家對生活未來的另類想象及無限的可能性。
城市或城市化進程對我們與其說是一個場景,不如說是一種隱喻的顯現(xiàn)。藝術(shù)家是一個城市的另類,他們的敏感、銳利和他們積淀的獨特而奇異的經(jīng)驗,他們的反思、批判精神,游戲化的幽默方式等等是值得關(guān)注的。新的藝術(shù)或許就在這種不確定的形態(tài)中產(chǎn)生,它是通過敏感到當代性和順應(yīng)時代潮流的藝術(shù)家以藝術(shù)的轉(zhuǎn)化方式來完成的,他們不僅是對某一文化景觀的觀察者,更成為幫助擴展其可能性的參與者。
但理想與初衷往往被現(xiàn)實處境的殘酷所摧毀。官方的展覽或由正式美術(shù)館承辦的大型展覽在規(guī)范化、系統(tǒng)化以及經(jīng)驗上來說,具備舉辦相應(yīng)條件,所以在策劃與操作上比較順遂。而由民間資本贊助的展覽,以這次第二屆成都雙年展的籌辦為例,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關(guān)注和為今后策展謹慎對待現(xiàn)象及問題。一是當商品和消費已經(jīng)全面占有我們的社會生活時,人與人的關(guān)系經(jīng)歷了從存在到占有然后到炫耀的演變。
原來那種以政治強制和經(jīng)濟手段為主要得管理方式已經(jīng)被文化意識形態(tài)控制所取代,通過文化設(shè)施和大眾傳播媒介構(gòu)筑的彌漫于日常生活中的偽真實出現(xiàn)。藝術(shù)家或獨立策展人的任務(wù)就是向大眾澄清他們無意間的整個社會的日常倫理標準,以拒絕的姿態(tài)改變?nèi)粘I睿瑪[脫慣性,從而改變權(quán)利關(guān)系,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二是作為獨立策展人,盡可以嘗試著不同的策展方式,但其底線不能滿足于展覽的“實實在在”展出后,其自我意識和獨立策展立場被烏托邦的想象或幻想消解了。
其實這次展覽的主題與方式就是想探討利用大眾文化的機制、資源,展示出藝術(shù)家在對待大眾文化現(xiàn)象的藝術(shù)轉(zhuǎn)化的視覺出位,從而提升出獨立的判斷與思考。但是,一不留神,策展人和藝術(shù)家都成為商家功利性訴求的籌碼,淪為商家達到其商業(yè)目的的一個資源,甚至可悲地成為成都啤酒節(jié)、成都夜市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一個單元,被商業(yè)“轉(zhuǎn)化”為無意義的表演式的消費“景觀”。三是在中國當下流行的幾種策展方式上,作為展覽機制的逐漸建構(gòu)過程中,應(yīng)杜絕民間資本贊助展覽后的隨意而為,或?qū)σ殉兄Z的原則、合同、事項出爾反爾;
同時作為民間資本在贊助藝術(shù)的過程中,起碼要具備承辦大型展覽的資格與條件。否則,縱使策展人提出了有價值的策展理念,參展藝術(shù)家的作品計劃也很充分,也難于實現(xiàn)。這次展覽的傖促、混亂以及開幕后的展示效果足以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目前各類展覽的策劃有與體制或官方、與民營資本、與藝術(shù)中心、與畫廊的合作,也有純民間的獨立策展等等方式。這些展覽陸續(xù)與普通觀眾見面后,“體制”終于不能再成為借口和理由,習慣以“反主流”形象出現(xiàn)的獨立策展人將怎樣面對這一新的策劃環(huán)境,怎樣在個人的策展特質(zhì)和大眾的需求中找到新的平衡點?
獨立展覽的價值在新的環(huán)境中應(yīng)當怎樣體現(xiàn)?獨立策展的基本立場和態(tài)度的底線在哪里?等等問題都值得策展人的反思和吸取其經(jīng)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