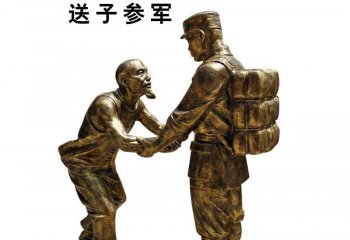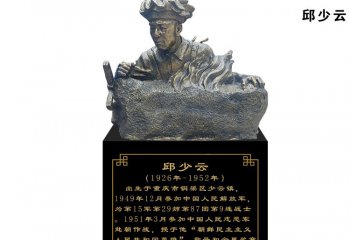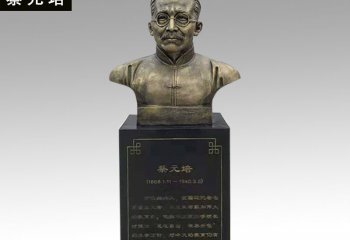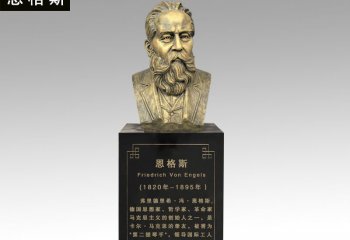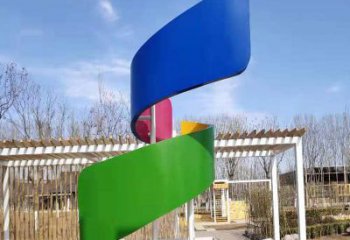12月13日是第五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上午7點整,升旗儀式準時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舉行。在嘹亮的國歌聲中,鮮艷的五星紅旗緩緩升起。國歌聲止,國旗又緩緩落下,降至半旗位,為死難同胞降半旗致哀。在南京市水西門大街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入口處,經過長長的雕塑廣場,每一個觀眾的目光都會被門前水池中一組雕塑所吸引,都被這些“無聲的吶喊”叩擊靈魂。這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組雕》,由著名雕塑家、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創作,雕塑刻畫的是南京大屠殺中承受了苦難的中國人的形象,他們心中巨大的悲痛、對戰爭的控訴和對和平的渴望,在雕塑中展露無遺。

這組雕塑已經成為同類題材的經典作品,獲“新中國城市雕塑建設成就獎”。近日吳為山分享了他當年創作這些群雕的心路歷程。記者: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大型組雕是您在2006年創作設計的,12年過去了,您還記得當時的創作狀態嗎?吳為山:創作這組雕塑時,我心情沉重,仿佛時間倒流到1937年那血雨腥風的歲月,那逃難的、被殺的、呼號的人民,那屠刀上流下的鮮血正滴入日本軍靴下…我恍惚走向南京城西江東門,這里是當年屠殺現場之一。一個民族不能忘記它的歷史,南京大屠殺給了中國人民巨大的創傷。

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我要用自己的創作來記住這段歷史。一個強有力的旋律在我內心油然而生:高起——低落——流線蜿蜒——上升——升騰!它對應著:體量、形態、張力產生的悲愴主題《家破人亡》,繼而是各具神態、體態、動態的十組人物《逃難》群雕,再繼而是由大地發出的吼聲,顫抖之手直指蒼天的12米高抽象造型《冤魂吶喊》。這組組雕的背景是以三角形體面為元素的主體建筑為背景,組成激越而低沉、悲慘而激憤的樂章,在進入紀念館前已受到感染。

走出紀念館,是和平公園,但見綠洲一片,在出口處長一百四十米、高八米的墻上以“勝利”為主題作浮雕墻。以“V”形為基本構成,分別以“黃河咆哮——冒著敵人炮火前進”和“長江滔滔——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為內容作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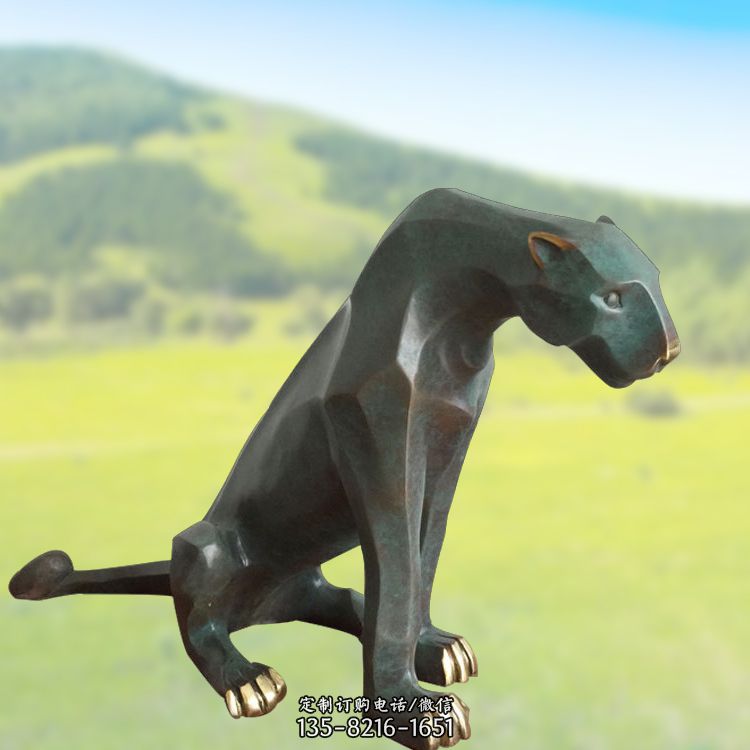
整組雕塑,采用刀砍、棒擊、棍敲與手塑相并用的塑造手法,其雕痕已顯心靈傷痕,是民族苦難記憶,是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罪證記錄。強烈的悲與憤的情感,產生了雕塑創作的速度與力量,我在38度高溫酷暑的露天勞作,深夜連續十多個小時的創作,在《辛德勒名單》主題音樂的回響中完成每一個形象,將藝術家情感和民族情感、人類情感的相融,并將此投射到作品。

創作靈感和激情從心底、指尖自然奔涌出來,為此,我還飽含深情地寫下幾句詩,作為作品的句號,銘刻在石碑上:記者:聯合國第八任秘書長潘基文曾評價說:“吳為山的雕塑作品蘊含的不僅是一個國家,更是全人類的靈魂。”在這組群雕中,怎樣體現國家和世界的關系,怎樣突出人類和歷史的高度?吳為山:在創作上述群雕前,我曾查閱大量史料,還走訪了常志強、夏淑琴等幸存者,從大量歷史照片和人物故事中感受到悲苦中人們的吶喊。我要通過藝術語言,告訴全世界,我們的民族曾遭受過的危難,以及普通民眾在災難面前的掙扎和吶喊…

有了這個立意和立場,除了站在南京看待這座城市的血淚,同情當年市民的苦難遭遇;站在國家民族的方位,看待吾土吾民所蒙受的劫難,我更立足于人類、歷史的高度來正視、反思這段日本軍國主義反人類的罪行,升華作品的境界,超越一般意義上的紀念、仇恨。回顧一下我國自20世紀至今所有表現抗戰題材的作品,幾乎是再現場面。那種國仇家恨溢于作品的內容與形式,這是時代的必然。但今天的中國日益強大,今天的世界日趨文明,中國有自信來傾訴歷史的災難與蒙受的污辱。

作為受辱者,中國有責任控訴戰爭,有責任告訴世界,和平是人類精神所棲。一個遍體鱗傷的弱國是沒有能力祈求和平的!因此凝固平民悲愴的形象,表現祖國母親蒙難,呼喚民族精神崛起,祈望和平應當是整個作品的表現核心。類似世界近代史上的慘案——奧斯威辛集中營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在未來人類會重演嗎?以史為鑒,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程的擴建是歷史的需要,是人類的靈魂工程。

擴建工程首先是建筑,它是載體,也體現精神;物證陳列是基礎;雕塑,凝固歷史,鑄造國魂,直接進入人心靈,為人們對客觀史實的認識提供價值判斷之參照。和平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得以建立的前提。銘記歷史、珍愛和平,是人類共同的期望。

我們銘記的不僅是一個民族的歷史,也要銘記人類的歷史。今天,人們走進莊嚴肅穆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會感覺這組雕塑組成了波瀾起伏的樂章,它們表現苦難、控訴罪行,但又從全人類的立場上表達正義必勝的信念以及呼喚和平的心聲。記者:這組雕塑從苦難升華出和平,從歷史中讀出未來,藝術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什么?

吳為山:整個組雕,沒有出現一個日本侵略者的形象,皆表現我遇難同胞,是為紀念我同胞而塑魂的。它的潛臺詞則為: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2014年這組作品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時,展名被定為“塑魂鑒史”,這就是我想傳達給觀眾的創作主題。現在我到世界各地辦展巡講,都會講到這一組雕塑,世界上許許多多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人,看到這組雕塑,了解南京大屠殺歷史,都會流下眼淚。
藝術超越了語言和國界,這組雕塑因其藝術表現力和深沉的人類情懷,震撼了來自世界各地觀眾的心靈。這組雕塑在世界范圍內引發靈魂的共鳴,正是因為其表現的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切,對全人類前途的關切。人類文化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建立在和平、發展基礎之上的,藝術作品中所蘊含的歷史、文化、情感及審美,往往是一個民族的根本價值所在。
而藝術作品的美及其創造智慧,則常常是超越國家、民族,成為人類共同的財富,就這一點而言,藝術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紐帶,而和平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吳為山教授的藝術,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東方藝術家如何以具象藝術和現代視覺藝術表現世界,如何在泥土與青銅中鑄就靈魂。為此我想起了二十世紀意大利象征派雕塑家杰阿柯莫·曼祖,他在強韌中具備感性古典的氣質,他簡潔單純的雕塑風格,喚起人們對殘酷戰爭的回憶。
吳為山則是在流動的形體中構建了自然生命的永恒,其簡約的造型表現了遭受劫難中的民族同胞,深刻地展示了悲劇的力量。這種跨世紀的東西方藝術比較和藝術家的對話,使我們確信藝術是溝通的橋梁。大型紀念雕塑,特別是紀念重大歷史事件的雕塑,是我們理論研究者應該研究的對象。從世界范圍來說,建筑師在設計建筑形象時,往往把雕塑作為一個點綴,這和他的修養、對藝術的認識、對藝術的鑒賞能力,以及對整個藝術的評判尺度有關系。
而好的建筑師,大都能夠理解雕塑家、畫家、藝術家,將創作組成一個整體。主題性雕塑,大型歷史紀念碑的雕塑怎么來處理“南京大屠殺”這個主題?怎么來揭示這個事件的意義?既要再現災難本身,又要表現受難人民的反抗精神,還要傳達出人民勝利的信心,這都是要在這組雕塑體現出的主題思想。吳為山和他的團隊在這方面做了很好的思考,也有很好的構思,值得我們研究。就雕塑語言來講,吳為山所提倡的寫意性雕塑,正是在發揮中國傳統雕塑語言的特點,其藝術語言本身值得我們思考。
現在很多年輕人已經淡忘甚至遺忘了那段苦難與抗爭的歷史。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句話是沉甸甸的。吳為山作品的重要意義就是再度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我們民族遭受過的這段苦難。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這個雕塑非常有意義,它既是我們國家進步、強大的體現,也是我們新一代的雕刻家在新的形勢下創作出新的優秀作品的標志。